|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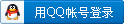
×
本帖最后由 陈林森 于 2012-6-25 08:07 编辑
I was born
陈林森
同样一句话,有时在中英文里,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比如,在中文里,“我出生了”,是一个响当当的主动句,说此话时,就像用湖南话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样,幸福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是,在英文里,这句话却是用被动语态表达:I was born——我被生下来了。说此话时,就像用四川话说“碗打破了唦”一般,充满无奈和痛苦。
中国人的“我出生了”,就像《西游记》开篇写的石猴出世一样,自个儿从花果山上的仙石里蹦出来。而按I was born这一表述,人的出生却是一个偶然事件。想想吧,浩瀚宇宙之间,茫茫人海之中,单是我的父母由相识相知到恰好生下了我,就已经是一个分母大得如恒河沙数的概率了,而由此上溯,世代相传都恰好指向了我,意味着我的被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一个关于偶然性的神话。不单如此,我之出生的空间和时段,都是无法选择的机率。为什么不出生在古代,又为什么不出生在30年之后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这一切都无法冥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的血脉中滚动着哪些先人的基因,多少悲欢离合才造化了我的生命个体?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全部包含在I was born这一简单的短语之中。
我在《戏说资本先天论》中说过: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一出生,很多问题就已经决定了。在过去的某个红色时段,有一句针对“出身”不好的群体的口号,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那个岁月,这前一句话是那样的刚性和铁面无私,让一大批人陷入了社会处境的尴尬。他们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仅仅是到近郊的农村还是到边远的山区,到街道工厂还是登上支边的列车罢了。I was born的一个特殊的年份,让我高中毕业赶上了那场狂飙的爆发,让比我早一年的师兄成为“末代大学生”,而我则成为光荣的首届“知青”,到而立之年后再一步一步地填补失去的青春,将所有的人生经历推迟了十年(这十年现在已经成为讳莫如深的黑洞)。而那个十年原本是人生最辉煌的十年,荷尔蒙和激情最充沛的十年。
I was born,我,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我们,不能选择出身,不能选择肤色,不能选择由血缘遗传和代际继承所蕴含的一切:财富、资源、外貌、性格、气质、智商……这种不能选择却与生俱来的事实的总和,在作为人生的前提和出发点的意义上,就构成了所谓的命运。
我看到哲学家叶秀山的自我介绍,说他一辈子运气好,别人说他“好事都沾边,坏事都擦边”。1952年参加高考,赶上大学扩招,到了什么程度呢?报什么录取什么。一个同学外语才考3分,也录取了。一个打架斗殴的混混,也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班上成绩最一塌糊涂的去了上海俄专。1956年大学毕业,是分配最好的一年,那一年重视知识分子,党号召向科学进军,后来一年比一年差,论文答辩的时候,别的教授都不喜欢他,偏有教授贺麟喜欢他,就把他要到社科院来了。第二年反右,他年轻啊,那些老家伙都批不过来,没成右派。文革也没被斗;1980年45岁,正是年富力强,赶上了出国的机会。其实,在羡慕之余,我们也得感谢生活的夹缝,让我们的社会保存了一批幸存者,保存了一批精英,让他们避免了因为“I was born”而可能遇到的一切变故和灾难,成为社会延续和文化传承的一批中坚和骨干,使社会不至于完全断裂。
当然,今天,更准确的说,在一个合理的社会,每一个人的I was born,才改变了曾经的恶性不平等。I was born,我的被生,不管是否受到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的欢迎,它也是一个无情的存在。在人的出生的奇迹面前,所谓身份、性别、籍贯、财富状况以及一切先天决定的因素,所有这些差别都不值得一提,都不能对人的被生和作为人的高贵的平等性构成挑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才成为可望而可即的梦想。权力与资本纠合在一起形成的“既得利益”将受到监督和约束,直到瓦解。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应当享受作为人类这一奇迹共同体一员无差别地接受社会关怀的权利,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十七大报告的庄重承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社会可以听得见的脚步声并成为社会发展方向。公平与正义像一面旗帜在我们社会的上空高高飘扬。不能仅仅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就与“国民待遇”无缘;不能仅仅因为我出身贫寒,就被剥夺了接受构成现代社会最重要资源——教育资源的分享;不能仅仅因为我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就坐视我的生命之花的黯然凋谢;不能仅仅因为我的肢体残缺,就不能享受一个正常人能够享受到的人的尊严;不能仅仅因为我衣服上有泥土,就不能得到公共场所同等的礼遇和服务;不能仅仅因为我没有政治的荣耀和显赫的地位,就被驱逐出发表言论的公共论坛;不能仅仅因为我有过灰色的记录,甚至仅仅是父母有过灰色的历史,就在我的手臂上佩戴耻辱的“红字”。是的,医疗对人的身体性呵护,教育对人的精神性抚慰,法律对人的权利性护卫,经济对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资源性保障,政治对人的自由迁徙和身份置换所提供的规则性平等,因为事关制度对生命奇迹的回应与致敬,理应成为社会的底线承担,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合理诉求。
I was born,还意味着我的被生,只是上帝的率性而为,或者只是游戏之作,而并非如《西游记》所说,是“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所孕育出的“仙胎”。我们是带着缺陷投胎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所具有我也具有,在我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性的普遍弱点。因此,与命运抗争,超越自我,创造奇迹,这一类的箴言,可能只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懦弱,虚荣,屈从,势利,记忆不好使,智商不够用,不时地会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从根本上,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出微弱的光亮,而无从挣脱命运的罗网。由此带来的某种结果的不平等,我们无法怨天尤人,只好私下里抱怨上天的不公。
I was born,对于这一生命奇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心存感恩之情,感谢自然的孕育和父母的恩赐,感谢社会理性之光的照耀,感谢社会每一个共生共存的人。我们生存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享受着他人劳动和创造的成果,都在消费千百年间我们的先人所浇灌出的文明果实。当我们得到社会的庇佑和人性的关怀之余,也应以微薄之力和微弱之光,贡献给这个养育了我和我们的社会。
|
|
 [复制链接]
[复制链接]
 | 本站法律顾问:易胜华律师|手机版|小黑屋| 尚庐山(原星子网)
| 本站法律顾问:易胜华律师|手机版|小黑屋| 尚庐山(原星子网)